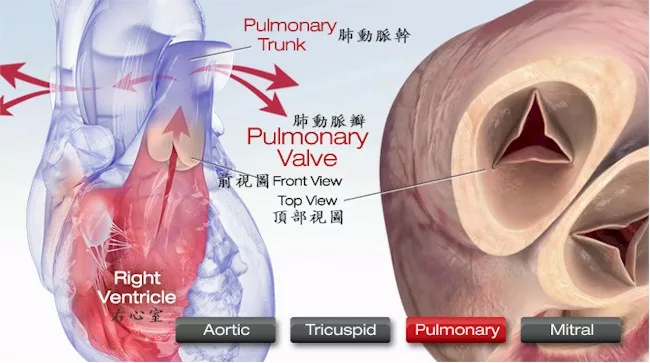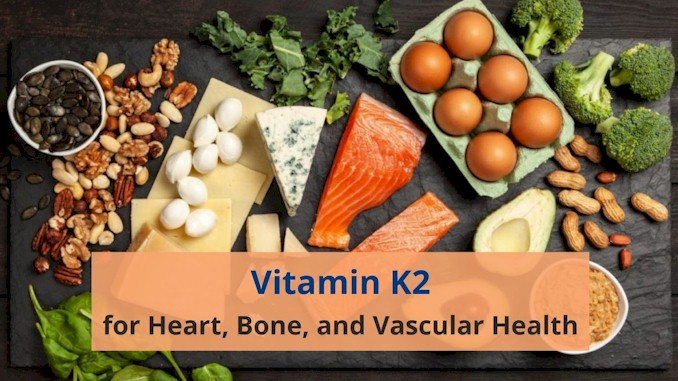1918-1920西班牙流感大瘟疫回顧
人類的歷史,大概有幾千年了。人類的文明也在持續的進步。但是,有些事情總是不變的,如人類的愚蠢和貪婪,以及永恆的循環。現在,世界人口超過77億,密集的飛行將地球變成了一個擁擠的小村落。2019年年底,又開始爆發了瘟疫,一種新型的病毒,在短短地2個月裡,病毒已經開始在超過75個國家傳播,大瘟疫已經拉開了序幕!
我周圍的人,普遍地,都認為它會很快結束。常在談話中說,等它結束後,我們怎樣怎樣…。我內心的直覺並不是這樣,我認為一切都才剛剛開始,整個人類世界正開始滑向深淵。我並不知道未來,但是,以前發生的事情,會告訴我們很多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作為人類,要去了解以前曾經發生過的事情—1918年到1920年發生的西班牙病毒大瘟疫的原因。
這是一個在當時造成2億人死亡的大瘟疫,當時的世界人口只有18億6千萬左右。也就是是,超過10%的人口因為那次大瘟疫往生了!!!現在,這個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們都不知道這次瘟疫的詳細情況,特別是中文社區的人們,其實,當時的瘟疫造成中國的大災難,對於這個其實不是離現在太遠的歷史,中文社區對它的記憶好像是空白。
1918-1920年爆發的大瘟疫,其實與現在爆發的新冠病毒很相似,為什麼,當你了解到在1918年到1920發生的事情之後就明白了!!!
1918年的大瘟疫是從什麼地方起源的呢?
1917年,在法國北部的一個英軍基地爆發像感冒一樣的傳染病。這個英軍基地位於沼澤地區,那裡有很多的水禽和豬。當人和生病的水禽和豬密切的接觸後,傳染病就爆發了。
另外在東南亞,還有另外一種有關呼吸道的疾病在士兵中間傳染,這些士兵參加了1916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大多數的感冒就源自東南亞。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正是這些士兵將病毒帶回到了歐洲。
總之,官方認證的首例西班牙病毒是從堪薩斯的美軍軍營開始的,那時,美國剛剛參戰。
那時,在堪薩斯州的哈斯克爾郡(Haskel County),爆發了一種看起來神秘的新疾病,當病原體從生病的豬身上跨越物種傳染給人時,社區中的人們,主要是農民開始染病。這種新的病毒,被稱為豬流感(Swine flu),它的傳染性很強,死亡率很高。當地的醫生被非常多的人死亡嚇壞了。他們跟美國公共衛生局聯繫,請求他們給一些建議。他們的擔憂被記錄了下來,但是,美國公共衛生局什麼事都沒有做。畢竟,那隻是一個偏遠的小鎮,在人口稀少的地區,病毒怎麼傳播?慢慢地,病毒傳播停止了,因為它找不到新的人傳染。
也許,這種事件再也不會發生,那麼我們的歷史也會不同。但是在1918年世界,是一個完美的,佈滿血的土地,非常適合世界範圍大瘟疫的爆發。
在1918年開始的時候,每一個軍事基地都擠滿了年輕人,他們在基地裡訓練,準備日後參戰。
軍隊使用所有可能的資源新建兵營、醫院、和訓練基地,那個小鎮的年輕人進入了位於堪薩斯Funston的軍營,就是當今的Fort Riley。那裡有超過56000人在那裡訓練。
那一年的冬天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天。很多年輕人都睡在帳篷裡,沒有足夠的取暖設備,只有一層薄薄的毯子。為了取暖,指揮官命令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個兵營裡,違反了健康和安全準則,這個準則規定了一個士兵必須擁有多大的空間。
來自疫區的年輕人也和其他人擠在一起,圍坐在火爐邊。他們已經開始咳嗽和打噴嚏。只用了6天,傳染病就爆發了。
來自哈斯克爾郡(Haskell County)的人是在2月28日到達軍營的。不到一個星期,大量的人開始出現症狀。僅僅幾個星期,整個兵營都被感染了。數千人染病,死亡38到50人左右。對於感冒來講,這是很高的死亡率了,但是,相比後來變異的病毒根本不算什麼。病毒後來發生了變異,變成越來越致命的感冒病毒。
病毒一般來說總是在持續地變異之中,但是在某個時刻,它會發生一個很大的變異。一個之前只會存在於動物身上的病毒發生變異,於是它可以感染人類。如果那樣的事情發生了,對於人類來講是致命的威脅。
病毒的傳染是像海浪一樣一波接一波的,這就是為什麼有流感季節的原因。在我們看起來,某種非常令人恐怖的病毒出現了,然後突然之間它又隱藏了起來。或者開始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爆發,感染那個地方的人們。接著,它返回來,比以前更加兇猛。
在1918年開始的西班牙大瘟疫中,發生了三波,毀掉了整個世界。第一波看起來並不是那麼糟糕,但是第二和第三波,卻超級的致命。
比如,在芬斯頓軍營爆發的傳染病在美國流感季節結束的時候就消失了,所以病毒的第一波爆發感染了很多人,然後就消退了。美國軍隊並沒有將之放在心上,因為他們正與死亡率更高的麻疹搏鬥。
流感病毒看起來消失了,但是它們實際上卻是傳到了其它國家。
在,1918年4月,裝載美國士兵的運輸船到達了法國的布雷斯特港,那個時候,正是爆發的流感疫情在芬斯頓軍營軍營消失的時候。
但是,傳染病卻開始在布雷斯敦傳開,並慢慢在整個法國北部蔓延。儘管如此,更多的部隊進入這裡,他們隨後被感染,然後又被送往其它的地區和前線。就這樣,軍隊將病毒帶往每一個他們穿越過的小鎮和村莊。
病毒就這樣傳遍了法國,然後穿越前線進入比利時和荷蘭,並傳染給敵人德國軍隊。病毒實際上對戰爭發生了影響,因為德國軍隊實在病得無法作戰。
然後病毒又由德軍傳給了德國人民。在1918年的5月,病毒進入了意大利,然後它跨越地中海進入非洲。另外,在1918年5月,它進入了英國。最後隨著士兵的靴子回到了美國。
被病毒傳染的人數和死亡的人數在葡萄牙和西班牙都開始像火箭發射一樣的高升。當病毒最開始在西班牙傳染,並出現很高的死亡率的時候,人們給病毒取了一個名字,西班牙病毒。
在1918年5月,有8百萬人死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班牙是中立國。所以它是第一個能夠自由報導有關病毒傳染信息,而沒有受到政府新聞限制的國家。大多數的國家並不想讓他們的敵人知道他們正與傳染病戰鬥,也不想因此影響國內人民的士氣。於是,政府對媒體施壓,要他們隱藏真像,並讓他們輕描淡寫病毒的嚴重性。
但是,在中立國西班牙,媒體能自由地、準確地報導發生的真實情況。在報紙的頭條對已殺人數百萬人的大瘟疫發出尖叫的時候,在其它的國家,人們只能悄悄地互傳有關流感的情況。
這時,世界開始認為目前的病毒的傳染情況比在西班牙的時候更加嚴重,而西班牙是唯一一個公開談論病毒傳染的國家。
西班牙病毒繼續着它的傳染進程,它在2018年7月跨越西歐進入斯堪迪納維亞和希臘;同一月,它傳入正在內戰中的俄國,這時,沙皇和他的全家剛被布爾什維克處決,布爾什維克正在與俄國其它的陣營打仗以獲得對俄國的控制權。
另外,在1918年的5月底,一隻有6個海員的船到達印度的港口孟買。接著就傳出碼頭工人生病的消息,接著其它碼頭的工人也開始生病。然後,碼頭旁邊倉庫的人也開始生病,就這樣整個城市都被病毒傳染了。
而那些離開被感染碼頭的船隻將病毒傳向亞洲的其它港口。
病人的人在孟買乘火車,將病毒沿著鐵路線傳遍整個次大陸和亞洲大陸。
在相同的時候,病毒開始從上海向中國內地擴散。在1918年的7月,病毒傳到了新加坡。新加坡是世界貿易的集散中心,這時滿是被病毒感染的碼頭工人,他們又傳染給本地的人民。
接下來,從新加坡繁忙的港口,航海者又將病毒傳到南邊的印度尼西亞,北邊的馬來西亞、泰國。
在1918年7月,被感染的海員將病毒還傳到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病毒還通過開往塞拉利昂的弗里敦(Freetown)的船進入西非;同時,通過達到肯尼亞蒙巴薩的船,病毒進入了東非。而到達開普敦(Cape Town)的船則將病毒傳入了南非。
從這些港口作為起點,病毒開始橫掃整個非洲,摧毀那裡生活的人們。
在1918年的7月,病毒還傳染到了秘魯,然後開始在南美傳播。
在1918年8月,病毒回到了北美。
在1918年10月,病毒傳到了新西蘭和日本。
在1918年11月,儘管對到港的船員進行了隔離,限制船隻入港,以及採取嚴厲的控制措施,病毒仍然開始在哥倫比亞、阿根廷、烏拉圭、以及智利爆發。
在1919年,澳大利亞也淪陷了。
在短短的不到一年時間裡,這種致命的病毒就席捲整個世界。
病毒之所以能這麼快而有效地傳播,有幾個關鍵因素。第一是世界大戰,人數眾多的軍隊在世界範圍內大規模的移動;以及軍隊中艱難的條件;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殘酷的,廣泛的使用戰壕,從而使士兵所在的環境相當的惡劣,造成病毒傳染的完美環境。大量的人生活在野外,忍受嚴寒、傾盆大雨和烈日的暴晒,他們蹲在骯髒的戰壕裡的時間長達數月之久,在那裡吃和住。而且每個人都靠的很緊。
在下雨的時候,戰壕裡會擠滿水無法排出,人們都泡在骯髒的水中。士兵們的腳開始在靴子裡腐爛。死去人們的屍體被放在兩軍對峙中間的無人地帶自行腐爛。雨水沖刷着腐爛屍體的地方,然後流到戰壕裡。另外,不斷爆炸的炸彈將各種臟東西都翻出來,並將大地變成沼澤。
在大戰結束時,超過9百萬的士兵和7百萬平民在戰爭中死亡。
因此,當一種的新的致命病毒出現並在全世界傳播的時候,它比敵人還致命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在1918年的夏季中的某個時刻,病毒發生了變異,變得比以前更加致命。
一些被感染的人會出現普通的感冒症狀,如發燒、發冷、噁心、身上痛以及腹瀉,很多人生病了,然後痊癒,就像得了普通的感冒一樣。而另外一些人則生病的時間更長,在被二次感染後死亡,如肺炎。
但是,很多人的症狀則非常嚴重,並且很奇怪。根據發表在1918年的7月醫學雜誌《柳葉刀》(lancet)的論文,醫生們爭論說,這種奇怪的瘟疫不可能是流感,因為症狀完全不一樣。意大利的醫生也爭論著相同的問題,對於一些人來講,西班牙病毒會造成他們出現高燒,並導致嚴重的肌肉痛,讓醫生認為他們患了登革熱(或被稱為斷骨高燒),它使得一些人暫時或永久的失明、失去聽力、成為殘疾。有些人失去了嗅覺、有些人出現眩暈、如果他們試圖自己行走的話,他們會跌倒。
另外,有些人還會出現非常快速發展的耳朵感染,從開始耳朵痛,到耳鼓的破裂只需要幾個小時。
有些人則出現非常劇烈的頭痛,眼睛看到的影像出現雙影;並在上呼吸道產生大量的膠狀物和腫脹,使病人呼吸困嫩;有些人咳嗽太厲害,以致將他們腹部的肌肉都撕裂了。
醫生們對病亡的屍體進行了解剖,他們發現病人的肺完全被破壞了,使他們看起來像是在戰爭中吸入了毒氣一樣。
而還有一些人出現的症狀,醫生們幾乎都從來沒有見到過。根據一個護士的描述,從肺部和眼淚中滲出的氣體在病人的皮膚下面形成一個一個的包,佈滿病人的全身,而當病人移動的時候,這些包就會像米脆一樣破裂開來。
有些病人則出現出病毒性出血熱的症狀(viral hemorrhagic fever),就想伊波拉病毒一樣,病人出現身體出血的狀況。
一份軍隊的報告描述說,西班牙病毒會快速拉升感染的程度,病人的肺被切成碎塊並咳出血,一般會在24到48個小時內死亡。他們的鼻子、耳朵和眼睛處會流出血來。
1918的西班牙病毒造成病人吸不到氧氣,於是皮膚變成藍色,甚至是黑色,就像黃萎病一樣。人們甚至區分不出白人和黑人。因此,在那個時候西班牙病毒還得到了一個暱稱,藍死病(blue death)。很多人都在問,是不是黑死病又出現了。
當病人的皮膚開始變成藍色,醫生就知道病人離死亡只有幾個小時了。
西班牙病毒是如此的令人恐懼,是因為會很快的將人殺死。很多病人都在染病後並出現症狀的1-2天內就死亡了,有的甚至在幾小時內就死亡了。
在一本叫著《the great influenza》(大流感)的書中回憶到,一個在南非開普敦的男人上了一輛公車,結果在他這次3英里回家的旅程中就遇到駕駛員死亡,另外公車上有6人死亡。當駕駛死亡後,他跳下公車,然後走路回家。
有很多的案例,那些很健康的人們在12個小時內死亡—Charles Edward Winslow,耶魯大學的流行病學家和教授。
1918年的夏季,病毒又重新回到了美國,但是這次病毒變得更加致命了。在1918年8月,滿是病人的郵輪達到紐約,此郵輪是從歐洲發出的,上面有4人已經在海上死亡,另外穿上超過200個人已經開始生病了。到岸後,他們被送往醫院,但沒有對他們實施隔離措施;
在接下來的幾週裡,更多的船達到了,上面滿載病人。同樣的情況發生在其它的深水海港,如波士頓、費城、新奧爾良。同時,在病毒從這些港口開始擴散時,這些船離開港口前往加拿大、中美洲、加勒比海以及南美洲,帶著感染了病毒的人們。
在1918年9月初,在波士頓的海軍碼頭傳染病暴發了,碼頭被封鎖了起來,但是,海軍軍官仍然在基地和碼頭之間通行。一個海軍軍官可能是將病毒傳向附近的Devon軍營的人。
在最初,只有少數人被報告生病了,但是幾天後,病毒感染暴發了。到了9月中旬,數千人被感染,大多數症狀都非常的嚴重,因此75%的人都需要住院治療。大量的病人立即對軍隊醫院的資源造成超載的狀況。因為軍隊醫院被設計的時候,其負載就是同時容難1200個病人,而在那個時候,有超過6000人擠進了醫院。於是,在醫院的每一個可用的空間裡都堆滿了病人,如走廊、辦公室,甚至是在外面的迴廊。醫生和護士都開始生病了,醫院裡甚至開始沒有足夠的健康人去照顧那些生病的人。很多人死在了醫院裡,醫院的太平間容納不了眾多的屍體。人們將屍體重疊在一起,就像門廳裡堆積的柴火一樣堆積在太平間的外面。每天,車都來拉走屍體,每天屍體都會再次將門廳堆滿。
美國軍隊的醫療官發布了一個命令,任何人不能去Devon軍營,或是離開那裡。但是,這個命令並沒有其作用。一部分軍官離開了Devon軍營,去了伊利諾斯州的Grant軍營,儘管那違反被頒布的命令。因為軍營裡的營房有限,這又導致很多人擠在一起,為病毒的傳播提供了理想的條件。在這些軍官到達Grant軍營後不久,他們就開始生病,人們將他們隔離起來,但是已經晚了。在第一個人生病後的2天裡,病毒就傳遍了軍營;在第四天就有人開始死亡了;在第5天,醫生和護士開始生病並死亡;在第6天,已有超過4000人住院,最後他們將軍營裡的10個營房變成了醫院;第7天,藥用完了,包括消毒藥劑和其它的藥劑;第9天,另外9個營房被改成醫院,於是已經有20個兵營被改作醫院。他們沒有足夠的床、被單和救護車,他們將稻草塞在被單裡來用作床墊,但是仍然不夠。他們為了避免傳播病毒,讓盡可能多的士兵戴上口罩,但是很快他們的布就用完了。紅十字會在軍營裡設立了一個站,主要是通知那些正在死去或已經死去人的家屬或愛人有關他們的情況。
接著,大量這些人的親屬湧進了這個死亡的流行病區,健康的家屬被咳嗽的人帶領著去太平間認屍;他們艱難的跋涉在擁擠的醫院裡以探望他們所愛的人。絕望的父母和妻子,企圖賄賂護士和醫生,以望他們能給予他們所愛的人特別的照護。這很快就變成一個問題,以致官員發出關於接受賄賂的警告。
然後。這些士兵的親屬又離開兵營,將感染的病毒帶向當地社區,市中心以及跨越州境的火車,最後回到他們的家鄉。健康官員發布了對Grant軍營的封鎖命令,但是已經晚了,病毒已經開始向Grant軍營外擴散。
在Grant軍營的第一例感染發生後的第四天,一列載滿士兵的列車從Grant軍營出發,跨越州境,去佐治亞州奧古斯塔的Hancoak軍營,整個行程大約在1000英里左右。車廂裡擠滿了士兵,而且通風很差。有人開始咳嗽,然後發燒,接著眼睛和耳朵裡流出血來。士兵們迅速地相互感染,很快病毒就席捲了整個列車。同時,在列車的行程中,經停很多的地方,士兵在停車時會出來購買東西,當地的居民會好奇過來觀看他們,鐵路工人被感染了,接著是居民。就這樣,這列車將病毒沿路傳染給一個接一個的城鎮。當列車最終到達佐治亞州的時候,3000人中的2000人已經病得非常嚴重以致必須送醫院,然後他們在Hancoak軍營引發了新的病毒大爆發。
歷史學家們不知道那列火車上究竟有多少人死亡,但是一份來自萊昂納多.伍德要塞的報告(Fort Leonard Wood)說,大約10%的人死亡。但是,當時的情況是,當很多人死亡,醫院的護士已經停止仔細地記錄死亡的人們。
當時美國醫療協會雜誌曾在其文章中說,“一個強健的人在下午4點中出現症狀,在第二天上午10點死亡”。
相同的故事在美國的很多軍營都在發生,在密西根的Custer軍營,在僅僅一天中,就有2800名士兵生病。
軍艦上的傳染病
而與此同時,數万的士兵仍被送往歐洲。不過這時,政府已經知道此病毒的流行是多麼的危險,所以他們試圖在船上控制病毒,那些已經表現出症狀的人不被允許上船,但此措施並沒有發揮什麼效用。西班牙病毒的潛伏期有數天之久,在被感染的人出現症狀之前,他們已經具備感染其他人的能力了。
在船上,仍然有很多人開始出現病症,於是他們被隔離在船艙裡,而且還有專門配備武裝的憲兵確保隔離。在大多數的船上,大約有400人被隔離在擁擠的、通風不好的船艙裡。儘管如此,他們卻仍然與船上的其他人共享船上的食堂,呼吸著同樣的空氣,觸摸相同的桌子和凳子的表面。
一艘叫著利維坦號(Leviathan)的軍艦上,即使實施了隔離的措施,病毒還是迅速地傳染開來。在2天內,艦上的醫療系統就不堪重負了,醫生和護士與他們的病人躺在一起,劇烈的咳嗽,血從他們的身體上湧出來,血在地板上形成了血池,那些仍然健康的護士必須跋涉過血池,他們的粘血的腳印留在地板上。最後,生病的人還多,他們只好躺在軍艦的外甲板上。他們甚至躺在艦炮的周圍,因為健康的人已無力搬動他們,而生病的人也無法移動自己。
當第一個死者出現時,軍官還仔細地在船長日誌中記下他的名字、死亡的日期和時間、軍階,死亡的原因。但是,離開紐約港僅僅一周之後,因為死亡的人太多了,軍官只記下名字和死亡的時間。
在船長的日記中,臨晨2點記錄了一個死者,然後是2:02又記錄了另外一個,在2:15分記錄了2個;死亡的記錄就這樣持續下去。仍然健康的人充滿了恐懼,他們困在充滿死亡病菌的船上,沒有地方可以逃。
他們開始將死者海葬,起先,他們還會舉行一個儀式,到後來,他們只讀出死者的名字,然後念一段很短的祈禱文,就將屍體滑入水中。
相同的事情發生每一艘運送士兵的船上。醫療顧問請求軍隊停止運送士兵,但是,戰爭需要更多的人加入。
同時,病毒也感染了平民,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或沿著鐵路線。
費城故事
但是,最糟糕的狀況可能發生在費城,因為管理的無能,其領導人無視來自公共衛生官員的警告,如果費城及時實施了有關的公共衛生措施,可能不會死那麼多人。
在1918年的時候,費城湧入了很多的人,因為鋼鐵、港口、鐵路以及工業需要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就業機會。但是,費城卻沒有足夠的房子提供給那些大量湧入的窮人們住,這些人於是擠在骯髒的貧民窟裡,那裡沒有門,下水系統。很多家庭住在同一個單位裡,幾百人共用小巷通道上的一個廁所。有時,很多人不僅同住在一個單元裡,還共用床,甚至睡在船上。還有招待所以每次6-8個小時出租床位,一個工人從床上醒來去工作後,另一個工人就會來在相同的床上睡6-8個小時,接著是另一個人。貧民窟裡所有的街道都骯髒透頂,到處是會導致生病的動物和昆蟲、臭水溝裡滿是吃垃圾的動物以及人的糞便。
同時,居住在這裡人都是工人,他們每天都勞累得精疲力竭,因為貧困的生活條件而非常的虛弱,這裡是病毒大流行理想的環境。
在1918年9月中旬,一艘船達到了費城的軍港,在短短幾天內,海軍醫院就被不斷湧入的病人擠爆了。這時,海軍就將病人送往平民的醫院。當那些海軍開始死亡的時候,西班牙病毒已經感染了費城的平民。在第一個海軍病人進入醫院的2天後,多個醫生和護士病倒了,幾個小時之內,他們的病情就發展得很嚴重。
但是,費城的衛生部門不希望人民出現恐慌,他們隱藏實情,說疫情是可防可控的。一些海軍和平民死亡之後,費城的官方又宣布疫情到達了拐點,並且染病人人數開始逐步下降。其實,大瘟疫還沒有開始呢。
另一方面,聯邦政府正忙著通過戰爭債券來為戰爭籌錢。人們購買政府的債券,政府承諾以後會連本帶利歸還。每一個城市都有必須完成的,銷售戰爭債券的任務。費城因此舉行了一個叫著自由債券的遊行,以銷售債券。負責公共衛生的醫生懇求政府取消遊行,因為它會造成病毒的大流行。但是,政府沒有理睬他們的請求。
在1918年的9月28日,成千上萬生病的人們擠在街上觀看遊行,他們擠在一起,只需要少許咳嗽、打噴嚏的病人就能造成病毒大爆發。僅僅76個小時後,費城的31個醫院裡的床位就被病人沾滿了。醫院使用簡易床擺放在過道裡、辦公室以及陽台上,以容難更多的病人。在有的地方,病人不得不與已經死去的人一起躺在地板上。當死人被抬走後,新的病人會佔據剛才那個地板上的位置。
費城還建立很多臨時醫院,但是仍然不夠。醫院開始拒絕接收病人,人們排在醫院外面,祈求住院,有些人就死在隊列中。即使那些住進醫院的人,對於很多人來說,醫護已經不存在,因為醫院的藥物已經開始短缺,醫生和護士們精疲力竭,他們開始逃離,去尋求幫助。
醫學院關閉了,那些上一年級的學生被召集起來,作為自願者進入醫院,去照護病人。一個學生在他的記錄中寫道,每天都有差不多1/4的病人死掉。
護士們精疲力竭,她們在那些還活著的病人但馬上要死亡的人的腳趾上掛標籤,這樣她們可以一次掛好幾個。一旦病人的皮膚開始變成藍色的,過不了幾個小時,那個病人就會死去。所以護士們非常有信心在那些病人的腳趾上掛上標籤。有時,有些病人根本沒有時間救治,很多人在感染後24小時內就死了。比如有一個在Mount Sinai醫院工作的護士,她上的是早班,但她不幸被感染,12個小時以後她就死了。
在費城舉辦了遊行的5天之後,因為人們持續地死去,政府終於開始行動起來,費城開始禁止所有的公共聚集,學校、教堂、劇院全部關門,卻讓酒吧可以繼續營業。但這些酒吧在第二天也關閉了,同時法院也關閉了,城市的公共交通也停止了。幾天之內,整個城市的運作都停止了。
僅僅在10天之內,費城就從每天數百人感染,死亡幾人,到每天感染人數達數十萬人,死亡幾百人的狀況。這都是因為人們並沒有聽從公共衛生當局的建議。
在遊行之後3週,費城的死亡人數已達4500人。這麼多的人死亡,所以沒有辦法立即安葬他們,因為挖墓坑的人也生病了,或者是拒絕掩埋那些因病死亡的人們。於是,屍體在停屍間、靈堂堆積起來。有些殯葬業者將他們的價格提高了50%,並只收現金。大多數殯葬業者的棺材都不夠用。有些還不得不僱傭守衛,因為有人偷棺材。
人們開始將死去的人用毯子包裹起來,或用麵粉袋裝起來,作為裹屍布。沒有人來搬運屍體,也沒有人掩埋這些屍體。所以這些屍體就只有呆在家裡,用被單裹起來,放在屋子前面的走廊裡,或者堆在小巷裡。在那些居住擁擠的單元樓中人們,因為一個單元要住好幾個家庭,他們沒有走廊放屍體,也沒有多餘的房間放屍體。他們就把屍體堆放在樓與樓之間的過道上。而還有些情況是,人們病得沒有力氣將他們臨床死掉的人搬走。
費城開始可以聞到屍臭,只要你在那裡,就可以聞到非常強烈的屍臭味,懸浮在費城的空氣裡。
於是,每一家人都開始自己挖坑來掩埋死者。每一個人都嚇壞了,他們都避免接觸任何人。有的家裡父母病了,他們的孩子們開始挨餓,但是沒有人敢去幫他們,因為孩子也可能感染了病毒。這開始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那些死去的人們的年齡大多都在20-40歲之間,他們大多數是父母。
食物開始短缺了,因為沒有卡車運輸食物到費城。費城的街道變得了無聲息,所有的商業都關門了,人們都躲在自己的家裡。公共交通停止了,警車也不開了,整個費城失去了它的生命。
William Sardo寫道,你處於持續的恐懼中,因為你看見很多你周圍的人都死了,你開始被屍體包圍起來。每當天黑下來的時候,你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第二天日出的時候。從日出到晚上上床的時間裡,整個家庭的成員會全部死光,沒有任何一個靈魂會留下。
費城的政府完全失去了功能,那些仍健康的人們,開始請求聯邦政府的幫助,但是任何幫助都沒有來。美國所有的城市都處在大瘟疫的壓力下,聯邦政府正忙於處理軍營裡,以及在歐洲爆發的大瘟疫。
在這個時候,城市精英階層家庭裡的婦女們組織了起來,她們中很多人曾參加了那次遊行的組織工作,她們開始去做管理這個城市的工作,她們找來公民領袖,一起計劃。她們設立了熱線,回答市民關於傳染病的問題。但是,很難找齊需要的工作人員,因為很多人都病了。她們選出社區的領導,這個這個社區領導可以組織食物的供應和醫療資源的分配;她們還在學校建立了廚房,並為病人送食物。那時,有500個人將他們自己的車捐出來,用作救護車和運送食物,或將醫生送到病人的家裡去。但是,自願者的人數遠遠滿足不了需求,很多人都害怕去做這些事情,因為他們害怕被感染。
帶頭人祈求人們的幫助,但是人們只是不理會。社會的架構開始崩潰了,這時,那些沒有參加自願管理城市會議的領導人終於開始加入了,最終,他們設法籌集了需要緊急資金,支付物資的供應以及醫護人員的薪水。他們派警察去清理那些堆積的屍體。(待續)